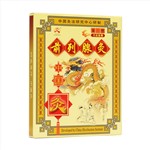柳叶刀:中国这一医学问题亟需重视!
中国健康人体内检出超级细菌“终极抗生素”还挡得住吗?
就在国人辞旧迎新的新春档口,顶级医学期刊《柳叶刀-感染性疾病》(LancetInfectiousDiseases)于1月27日在线连发两文,直指“中国多粘菌素耐药现状”。
其新闻导语如是说:在中国尚未临床使用多粘菌素的时候,耐受这一临床“最后一线”药物的MCR-1阳性大肠杆菌,已经在人群中流行开来。
“我们发现人携带mcr-1基因阳性率逐年升高,且病人和健康人都有检出。”其中一文的通讯作者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教授说。
另一文的通讯作者,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、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在接受《柳叶刀》访谈时表示:“携带mcr-1基因的菌株对多种抗生素仍保持敏感。这提示我们,要守住多粘菌素这道防线。”
中国没用过多粘菌素,为何会耐药?
多粘菌素是一组多肽类抗菌药物,包括5种不同的化学成分(多粘菌素A、B、C、D和E)。其中,仅多粘菌素B和多粘菌素E(粘菌素,抗敌素)曾在上个世纪短期用于临床,后因副作用大被弃用。
近年来,革兰阴性菌(如大肠杆菌、肺炎克雷伯菌、铜绿假单胞菌等)多重耐药问题日益严重,由之引起的感染几乎无药可用。这才迫使人们重启多粘菌素类药物,用于治疗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。
耐药菌产生的前提,是药物一直刺激机体,体内细菌为了生存而发生进化。但时至今日,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批准多粘菌素用于临床。既然不用,耐药基因从何而来?
早在2015年底,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健华和沈建忠院士的团队于全球首次提出,mcr-1是导致多粘菌素耐药的主要机制。
“上世纪90年代,多粘菌素被广泛应用于农业、养殖业,以防止农场动物患病等。”作为沈建忠院士团队最新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之一,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田国宝教授告诉“医学界”记者,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研究推测:多粘菌素在禽畜饲养中长时间使用→动物体内出现mcr-1基因→食物链→人体内出现mcr-1基因。
据《自然》杂志报道,中国粘菌素类药物用量尤其高,每年农业领域用量达1.2万吨。英国伯明翰大学微生物学教授LauraPiddock在针对上述发现时置评:“必须尽快将多粘菌素类抗生素的使用降至最低水平,停止一切不必要情况下的使用。”
是坏消息,但不应恐慌
纵观本次《柳叶刀》发布的两项研究,沈建忠院士团队给人“当头一棒”;俞云松教授团队则帮我们“揉了揉”创口。但他们都指出:“不应恐慌”。
建议删除危险系数中“和俞云松教授组相似”字眼,因为2篇文章的研究侧重点有很大不同。
“之前研究认为,多粘菌素耐药性都是由染色体介导,细菌通过复制将耐药性遗传给后代。而发现mcr-1的最主要意义,就在于mcr-1基因存在于质粒上,可以通过水平传播的方式在菌株间传递,进而大大增加了多粘菌素耐药性在临床传播的风险。”田国宝教授介绍。
揭秘:后续研究已有“悲伤”的结果
截至2016年底,包括欧盟、加拿大和美国等在内的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,相继发现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-1。或存在于动物身上,或存在于人群中。
下图是世界卫生组织于2014年发布的预测,至2050年,全球由于细菌耐抗生素而造成的死亡,将达到每年1000万人,超过癌症的死亡人数。亚洲作为重灾区,死亡人数占了近一半。
针对“无药可用”的恐慌,有的科学家主张加紧新型抗生素研发;有的强调抗生素合理使用和监管;有的认为应深入研究细菌耐药机制。
沈建忠院士和俞云松教授也透露了下一步研究方向。
“针对人际传播,我们可能很快会发布一篇新论文,证实mcr-1可能已在人际间爆发流行。”田国宝教授介绍。
“mcr-1基因的出现,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耐药细菌束手无策。对多粘菌素耐药,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抗生素耐药。我们担忧的是,mcr-1容易与其他耐药基因共存,由此诞生对多粘菌素和其他各类抗生素同时耐药的‘超级细菌’。而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为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,指导临床医生谨慎对待mcr-1携带者的临床治疗,谨慎评估患者感染mcr-1阳性菌的风险。”沈建忠院士指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