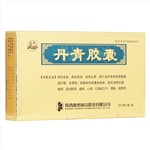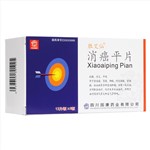癌症,是“众病之王”,治愈,是人类的心愿。
自2016年4月起,医生医事推出“遇见·肿瘤大咖”系列,每月一期,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,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,希望能对患者的抗癌之路、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有所帮助。
在此,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,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。
第二期
吴一龙
代表着肺癌历史上的“中国贡献”
在“遇见”这位肿瘤大咖之前,就被提醒:听完他讲话,绝对路转粉。
实际上,第一次跟访他的门诊,看他和患者恰到好处地开玩笑时,头一歪,嘴一噘,用拍照最萌的45°眼神看着对方如何接招时的“坏笑”,我就果断转粉。
全科病例讨论上,他也是“坏笑”着挑起“战事”,不停问“有没有不同观点?”直到医生们对化疗、放疗、手术方案争论不休,他最后结案陈词,思路之开阔、思维之敏捷,总有“神来之笔”,让人心服口服。
如此生动的吴一龙。
当年,这位我国肺癌治疗的领军人物,曾是医院班子换届的热门人选,他赶紧跑到省里表态:“千万不要把我选上去,我绝不当一把手”。如今说起这件事,他像个孩子一样大笑着调侃:“当官要当副,绝不当常务”。他只想搞专业,所以从担任中山大学第三医院院长调入省医当副院长时,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
如此真实的吴一龙。
他曾是“广东省肺癌第一刀”,精湛的手术技术让他名振江湖,而让他走向世界的则是药——他是肿瘤靶向治疗研究的中国第一人,被誉为“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”,国际尤其亚太地区晚期肺癌治疗原则、治疗指南,许多证据出自他领衔的中国专家之手。他如今更肩负着全球最前沿肿瘤新药在中国的临床试验,包括最近在美国前总统卡特身上创造奇迹的免疫疗法PD-1抑制剂。
60岁的吴一龙,人生最大的感悟是:“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该做什么,而且30多岁时就知道了。”
这是一位天生搞靶向研究的人,连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如此精准。
一个人发生巨大的转变,常常是上帝之手对心灵轻轻一拨。
对吴一龙来说,第一拨,发生在他30多岁时。
1988年他到德国留学。有一天下午,跟着老师去听第二天的手术安排。办公室里坐着两位白发老人,看起来像是老教授,因为穿白大褂的医生们都在边上毕恭毕敬地站着。医生们针对患者的片子、病情逐一发表意见,老师进行了总结。然后轮到那两位“老教授”做最后的陈述了,他们说,“听你们说了后,我知道了我的病情,知道了几种治疗方式,也知道了你们的态度和相应的利弊”。
原来,他们根本不是“老教授”,而是那次讨论方案的病人!最后他们选择了医生推荐的治疗方式。
吴一龙深受震动,“原来医生应该这么当,科学严谨地告知,让病人充分有尊严地选择、对待自己的生命。”
这一拨,彻底打开了吴一龙的人文观。从此,他的一切工作,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,完全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——患者,把自己摆进去。
门诊里,同样做一项有创的检查,他会这么问:我需要给你开一项检查,医生会从你背部用一根针扎进去穿刺取组织做活检,你同不同意?
同样一句话,他会这么问:请把你的片子给我看一下,好不好?
同样给患者治疗建议,他会给出几个备选方案和他们商量,但他会充分表达自己的主见:换药,是一个选择,但从我的专业角度,这个放在后面,因为医生给你的建议一定是当下最佳、最适合你的方案。
同样是临床指南,他牵头制定的首部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》,颠覆了全世界的指南形式,不再是千篇一律地罗列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,而是针对性地提供中国不同地区的患者能接受的、益处最大的治疗方案,这其中包括经济上的、身体上的,心理上的和所在地区局限性的等。
他说:“当医生的所有工作,从人文角度去考虑你的研究对象、决定你要对病人采取的措施时,你的天地就变得特别宽,你能做出很多老百姓非常欢迎的改革和变革。”
在德国的这一年,是他人生观塑造最重要的时期,那段时间,他看到了博爱,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。
他说,真正的好医生,需要在任何环境里都能保守一颗纯朴的心。如今,中国医生人文缺失,要改变,不是一朝一夕,也不是靠行政文件、命令,而是要从根本的人性去塑造。
人性,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第二拨,发生在他从德国刚回来时。
1980多份历史病历,不仅改变了他的方向,使他从一名单纯的外科医生转而研究肿瘤的综合治疗。
1989年,33岁的吴一龙刚从德国回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,心高气傲却被学术界“压制”。
苦闷的他,想起了老师曾对他说的,“当外界不理解你的时候,不要跟他争辩,你就做自己的事情。”于是,他做了一件事——整理病历。
他向病案室借出病历,每天利用中午的时间研究整理,他把医院胸外科从建科开始保存下来的1980多份病历全部研究整理了一遍。
就像每一个少林弟子都要从扫地僧开始一样,有悟性的人,扫着扫着就豁然开朗了。
他从这1980多份病历中发现的问题,对他很震惊,也开始反思:当时曾让医生们因手术成功而沾沾自喜的病人,没几个月就死掉了,为什么?到了90年代,肺癌的5年生存率依然与60?70年代相差无几,为什么?
最后他豁然明白:现有的肿瘤治疗手段局限性太大,单一的治疗存在很大的问题,这条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,必须有所创新,要改,必须动用所有手段去治疗肿瘤。
从此,外科出身的吴一龙,在中国率先走上了综合治疗的道路。为了真正能患者提供综合治疗的方案,他在1997年,他率先提出一种新模式——单病种首席专家制,即由1个全才带领各种专才治疗肿瘤。作为医院肺癌的首席专家,他开始恶补影像、内科、放疗、转化医学知识,十几年后,他成为了肿瘤界公认的“通才”。
第三拔,则是一篇文献。
1995年,他看到了一篇英国文献,作者似乎也和他做了同样的事——整理历史病例。作者针对过去30多年的肺癌治疗进行总结,结论非常吓人:手术后加上通常认为是保险的放射治疗,没给患者带来好处,反而使死亡率增加了21%。
除了这个吓人的结论,吴一龙对文献是一头雾水,虽然文献里写着采用的研究方法叫做“个人资料的综合分析”,还画着“森林图”,但他根本看不懂,于是写信向德国的老师请教“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出这个结论?”
老师回信解释说,过去的研究只是依据少数病人的个人资料得出结论,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病人的数据都纳入数据库中进行计算。森林图的每一条线就代表一个研究群体,研究对象越多,结论越可信。
“这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。循证医学是遵循证据的医学,必须依据大量的病人情况。我们之前做手术大多依据经验,现在看往往是错的。”吴一龙从此萌发了对循证医学的兴趣,花了2年学习、“弄懂”这个问题。
他还让循证医学在中国全面开花。1998年,吴一龙在中国第一次开讲循证医学这门课,轰动一时。2000年,他创办了循证医学杂志,在中国推广循证医学,如今循证医学已被医学界普遍接受。
而循证对他来说,就是向历史学习,向每一位病人学习,是反思,总结,这成为了他的一种思维方式,并让他获益一生。
吴一龙说:“读书使人明智,反思历史,你会变得越来越明白;放到医学上,当医生学会对每一个病例进行总结和反思,你会知道需要改进什么。”
他从年轻时开始就有一个习惯,随身带一个小本本记下每一个病人,时不时拿出来思考。1999年,他还创建全国首个生物标本库,完整存留患者资料。
正是基于这一例例的病人,他率先发现了中国人身上特有的肺癌驱动基因有别于西方人,为中国的肿瘤患者带来第一个靶向药物,并让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长3年多,改变了全世界的肺癌治疗指南。
如今探索性研究成为了吴一龙的主要方向,他肩负着全球最前沿的肿瘤新药在中国的临床试验,手中的这些“代号”,是中国中晚期患者的希望。
他说:“5年后,让60%肺癌基因突变患者接受最佳靶向药物治疗,让肺癌真正成为慢性病,这是我的梦想和奋斗目标。”
而探索性研究更要有很多病人来参与、贡献,医生和患者是真正的伙伴。作为医生的吴一龙,更加感觉到病人的伟大,因为在这些研究背后,医生可能功成名就,而患者也许能从中受益,也许什么都得不到。
他说:“病人提供自己的样本,提供自己的经历,让你去总结规律,作为临床医生,当你认识到这一点时,再去思考医患关系,你对待病人就会有另一种态度。”
“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,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。理性和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,缺少了任何一个,医学都无法真正飞翔。”吴一龙如是说。